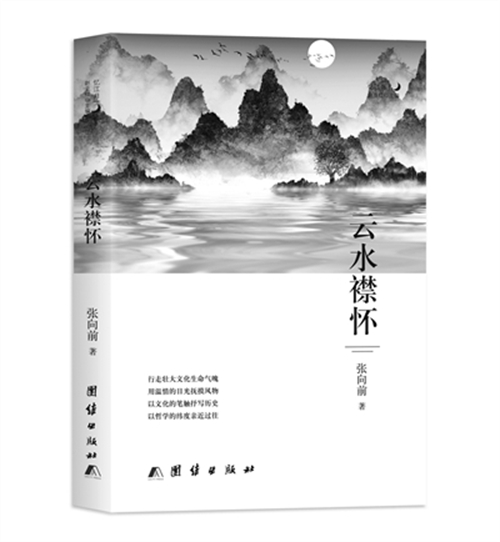伴随着旅游热的兴起,五花八门的游记也广见于各类报刊,自媒体更是大行其道,其中也不乏过目难忘的精彩篇章,但绝大多数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人云亦云、拾人牙慧之作,要么全景式的景区介绍,要么唯写景而写景,看不到景区的独特内涵与外延,特别是一些人文历史景区,给人印象并不深刻。所以有人说游记易写,信手成章,但深谙此道之人,却觉得游记难写,并不是几行华丽或抒情文字的简单堆砌,要写出一篇有自己面貌、思想和个性的游记,绝非易事。
散文作家张向前(笔名阿若)在这方面作了有益探索。近日,拜读了他的散文集《云水襟怀》,让我明白了如何从人们熟悉或别人已“写烂”的景物里,寻找独特或自己的视角,写出与众不同的东西,也就是写出新意。而所谓新意,就是在同样的景物里,另辟蹊径,写了别人没有写过或少写的东西,或者摄取景物中的某一细节或横断面,如一块石碑、一个人物、一件小事、一段悠远历史等,深挖其内涵,写出了自己的见解。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本人尝试写的一篇海南天涯海角游记——《神奇的雕塑家》,之所以能刊登在《南方周末》二版头条,也得益于自己能从专业知识的视角,将其写成一篇地质学科普散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而写出了新意,受到编辑青睐和读者好评。如今,学习了张向前的《云水襟怀》,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写作的努力方向。
古琴台与黄鹤楼、晴川阁并称武汉三大名胜,自然写者甚众,但张向前的《琴声何处》,却写出了别样韵味。他没有采用惯常写法,既没写古琴台沧桑,也没写从这里流淌出来的中国十大古曲之一《高山流水》韵律如何志存高远、优美动听,而只写了庙堂之上的大夫俞伯牙,与乡野之下的樵人钟子期一段相遇相惜相知的千古绝唱,亦所谓“高山流水有知音”也,让人顿感新鲜和好奇。“千年不遇的知音相遇了……两条平行线上的人偶然折向交集,两颗素昧平生的心悠忽合拍,竟然因着琴声振颤在了一起,同频跳动。”
在《壶口天地一弦琴》的篇章里,他把“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壶口瀑布作为打开思绪的窗户,将笔触伸展到天地之间,甚至黄河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在他的笔下,“黄河就像一川瀑布,几乎笔直地挂在内蒙古与河南三门峡之间”,“把山西与陕西分离,也把山西与陕西勾连,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血脉之谊”,“挽山连海,在行走中壮丽,在壮丽中升华”。这些意境开阔,又独具想象力的个性描述,就像“天地一幅画”“天地一弦琴”,予人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让人读罢不禁与作者一起发出“黄河,你几千里的不懈奔流,难道就是为了在壶口置琴弦歌,奏出天地人寰的最强音吗”的感叹,处处闪烁着文字魅力和思想光芒。
张向前书中的游记,大部分写的皆是古人留给今天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官渡、日月山、唐明渡、仓颉祠、退思园、雁门关、咸阳古道等。面对这些古老遗址或古老文明,作者往往会触景生情,睹物思故,最容易“发思古之幽情”,追忆历史、文化,将文章写成怀旧风或复古风,但在他的眼里,觉得这样写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更难从“老皇历”里翻出新意,做到古为今用,让读者喜闻乐见。因此,他的游记总是连接历史与现实,更愿意把历史放置在今天的日常生活里来观察,从历史中走过,从现实中走回,从而抓住过往历史与当下日常生活之间内在的隐秘关系这个鲜活视角,去书写古今文明,可谓别具一格,洋溢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
前些年,他踏访了史上赫赫有名的“官渡之战”古战场遗址后,挥笔写下了《官渡无渡》这篇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奇妙佳作,落墨于有渡与无渡之间,既目光辽远,又洞见眼前。“那条潺潺流淌的河水被发黄的历史册页洇干了,那座熙熙攘攘的官渡古桥也被时间的巨手抹掉了,消失在视线之外。”他透过远去的战争硝烟,看到了那场以弱胜强典型战例的“有渡”,更看到了今天的“无渡”。“昔日的古战场,如今已变成官渡桥村”。“官渡桥村成了省级文明村……住上了楼房、四合院……过上了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官渡人的心情,应该与当年官渡之战胜利后的曹操一样,爽朗舒展”,而“我更喜欢眼前的官渡,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像这样写“古”而不唯“古”的篇章,在书中比比皆是,如《晚唐的一缕霞光》《日月山口望长安》《昭君的背影》《云看横岭》等,均透过闪烁的历史光斑看到了现在和未来,让历史载上了时代的列车,更加熠熠生辉。
张向前是一位行者,更是一位写作的有心人,常把行走作为一种人生的修行或修炼,利用工作之余寻古问幽,踏遍青山,蹚水过河,而他足之所至,便思之所至,文之所至,既氤氲了历史,又愉悦了当下,更让人读到不一样的游记,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或许便是视角创造出来的力量。
陆悦